
▲賈平凹 郭天容/繪( 1/ 2)謝尚發(f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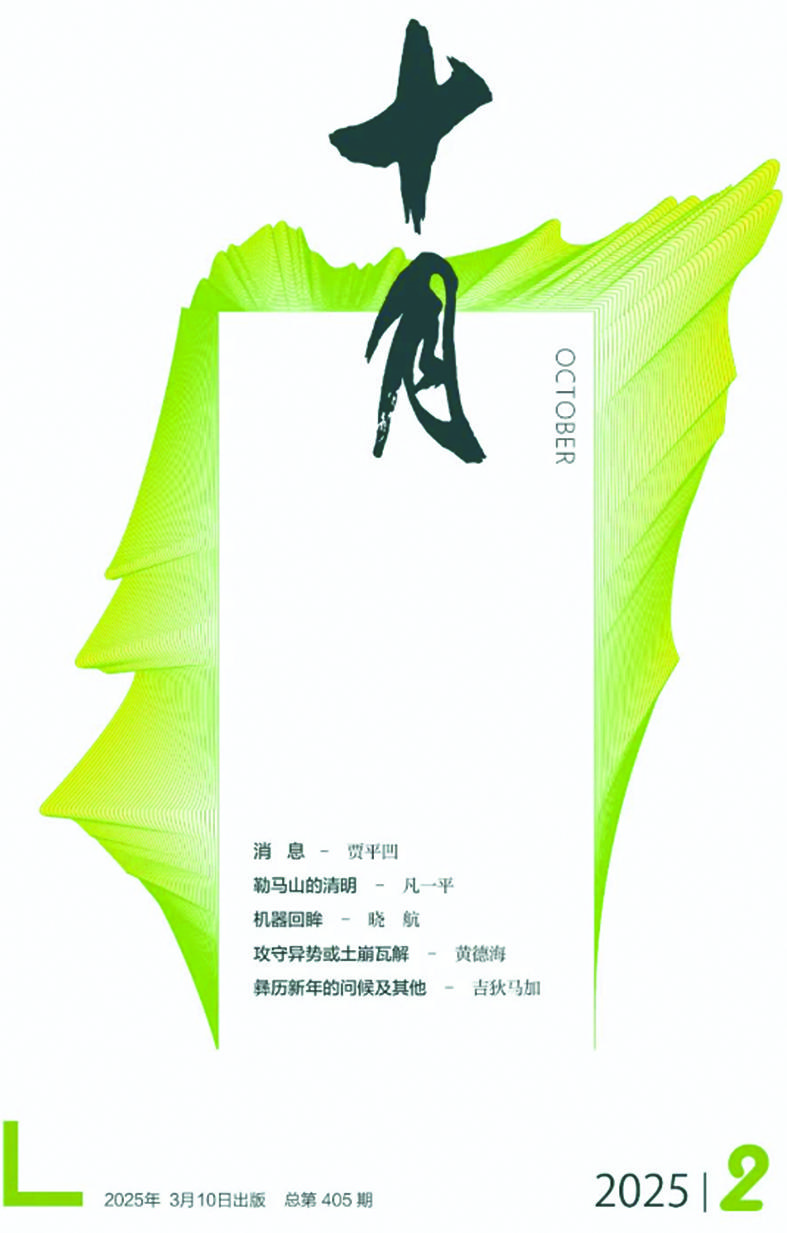
孔子在《論語·為政》第四則中��,針對人生不同階段所追求的目標��、達到的境界,由衷地感嘆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痹趯Α捌呤辰纭边M行解釋的時候����,錢穆強調:“圣人到此境界,一任己心所欲�����,可以縱己心之所至��,不復檢點管束�,而自無不合于規(guī)矩法度,此乃圣人內心自由之極致�,與外界所當然之一切法度規(guī)矩自然相洽。學問至此境界�,即己心,即道義�,內外合一,我之所為�,莫非天命之極則矣?���!睍r間法則之下,此種智慧之獲得����,既需要四十的不惑����,亦需要五十對天命的領悟�,經由六十的耳順之后,才能抵達人生境界的圓融�、完滿與通達。
不惟此�����,學問有此境界����,文學創(chuàng)作亦有此境界。那么如何將這一生命境界融入文學創(chuàng)作之中呢�?融入之后又會呈現(xiàn)何種文學風格呢?袁宏道曾在《敘小修詩》中說:“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魂�����,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獨抒性靈”是對前者的回答����,“如水東注”則是對文體風格的形容。針對后者�����,蘇軾曾在《答謝民師書》中更為形象地描述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tài)橫生?!?/p>
不管是從“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生命境界來說,還是從“獨抒性靈”的創(chuàng)作方式與“行云流水”的文本風格而言��,賈平凹的新作《消息》都鮮明地體現(xiàn)出一種“文學的自由的性靈”之格調與神韻��。1952年出生的賈平凹已然70余歲���,正處于人生“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階段�,其創(chuàng)作也就自然而然地會反映出此一生命境界的癥候�。這既是他自1973年便開始創(chuàng)作至今已超過50年創(chuàng)作生涯所遍歷的“不惑”、“知天命”與“耳順”的自然結果��,也是其甩開各種“管束”與“規(guī)矩法度”進入到全新寫作境界的體現(xiàn)�����。這是創(chuàng)作者的自由的極致體現(xiàn)��,亦能讓閱讀者于文字中感受到自由的暢然����。
如此諸種,誠如賈平凹在該書的《后記》中所說:其一���,“我已經是七十歲后的人了”�,“我是經歷過無數(shù)次劫難的�,已經不再那么慌張”;其二����,“我喜歡隨心所欲,去到哪兒是哪兒�,饑了就尋路邊店,或者敲開農舍����,掏錢讓人家給搟一碗面。晚上了��,縣城的賓館睡過��,街鎮(zhèn)上的小旅社里也睡過。那不是采風�����,可以說是流浪�����?���!逼淙耙蝗畏棚w縱欲了�,感覺紛至沓來……是意氣達適,是精神的自由翱翔了���?!逼渌?�,“你把它記下來�����,寫成文章,目的是帶更多人也進入異境�,喚起我們的情懷�。”從這些表述里����,也不難看出在撰寫《消息》時賈平凹的心態(tài)與文學觀念,它們自然也都反映在“文如其人”的作品之中��。
文體的自由:
審美性或文學性
若從閱讀者的第一觀感來看�,《消息》所呈現(xiàn)出的“自由的性靈”便是“文體的自由”,它凸顯為一種全新的文本格調與神韻的產生����,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恣肆灑脫的筆調”。一般來說���,文體是指文學作品中因創(chuàng)作者獨特精神氣質影響而促成的固定語言架構形式及其所呈現(xiàn)出的文風�����、格調等審美性質地���,以及固定題材與常用語言方式結合而形成的體裁規(guī)約,它們常體現(xiàn)為作品的氣韻。就文體的表層而言�����,它主要體現(xiàn)為文本的形式構成——語言的結構模式�����、特定的語體和語貌���、選詞造句等體現(xiàn)出的強烈個人色彩��,亦即桐城派所謂“辭章”:“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與言于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為辭,然后有聲音節(jié)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tài),彩色之華�����?!保ㄒω尽洞鹞虒W士書》)由表層更深入�����,文體第二層構成可稱之為“文章風格”��,即特定的語言����、修辭所呈現(xiàn)出的作品辭氣、格調與神韻�,及其所傳達出的作家的思想與觀念,它也正是布封所謂“風格即人”的判斷基礎����。文體構成最為深層次的則是體裁����,它是獨特的文本形式經年累月地沉淀出的獨特文體風貌�,且經眾人之手而形成某種“文類的共識與規(guī)約”。自近代以來�����,最常見的體裁劃分往往采用四分法�����,即小說�、散文、詩歌與戲劇——小說被認為是“一種側重刻畫人物形象�、敘述故事情節(jié)的文學樣式”,其特征被概括為“典型三要素”:“深入細致的人物刻畫��、完整復雜的情節(jié)敘述��、具體充分的環(huán)境描寫”���;而散文則被認為是“一種題材廣泛�、結構靈活�����,注重書寫真實感受、境遇的文學體裁”��,特征是“題材廣泛多樣���,結構靈活自由����,抒寫真實感受”(童慶炳)�。
如果將《消息》置于文體常識的規(guī)約里��,它會顯得“不倫不類”——在發(fā)表于《十月》2025年第2期時被標注為“長篇小說”�;隨后又獲得了第五屆豐子愷散文獎的特別獎。將之界定為“長篇小說”���,依據(jù)在于作品內部許多小片段實際上是各種“小說寫法”的體現(xiàn):鮮明的人物形象�����、充分的環(huán)境描寫����、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如第五節(jié)《集市》描摹游手好閑的懶漢偶遇野鬼日行而病倒的故事����,第九節(jié)《謝小白》講述了兩個鄰居之間的故事,第十二七節(jié)《桃花命》塑造了一個叫做麥香的女子的典型形象……�����;將之歸入到“散文作品”類別��,亦有充分的理由�����,它內里許多小節(jié)實則具備鮮明的散文文體特征:題材廣泛����、結構靈活、真情實感����,如第一節(jié)《黃河晉陜大峽谷》,純粹用了散文描摹的筆觸書寫地理地貌�,抒發(fā)一種來自大地的感慨,而到了第二節(jié)《倉頡廟》又將筆頭轉向傳統(tǒng)文化��,第三節(jié)《三河口》再轉為對純粹地理的描摹中偶爾涉及人物的行為……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消息》是一部典型的“筆記體小說”——隨意落筆�,不講究文體規(guī)范,以合適的文法隨時記錄下生活中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甚至隨意到無所寫而寫下類似于“地方志”的文字。典型者如第十二六節(jié)《商山道》單純記載一條古道��,第三十節(jié)《注水》又純粹是抄錄地方志來描摹渭河的發(fā)源地與流域狀況�,第五十節(jié)《涇河》與第三十節(jié)遙相呼應地解釋了“涇渭分明”成語的地理狀況……但似乎在這種書寫中��,將之稱為純粹的“筆記寫作”更為合適���,因為它如司馬光的《涑水記聞》�����、葉實《愛日齋叢抄》�����、洪邁《容齋隨筆》�����、陸游《老學庵筆記》等一般���。但其中又包括諸多“志人志怪”內容�����,如第二十節(jié)《海坪》講述了一個小人物的神奇發(fā)跡史�����、第十四節(jié)《李三四》塑造了一個小偷的人物形象���、第四十四節(jié)《好死》書寫的是名叫阮小手的人物跌宕起伏又波瀾不驚的一生、第五十八節(jié)《柳長馬》描摹一位鄉(xiāng)下能人的言行錄……將之歸入“志人志怪小說”的序列也毫不違和���,甚至可以看作是當代作家對《世說新語》《搜神記》等的自覺繼承與發(fā)展��。
從長篇小說到散文�����,從筆記體小說到史料筆記���,從筆記再到志人志怪小說����,《消息》自由地出入各種文體�����,隨性而起��,隨文賦體�����,其體越是散漫無所依��,其文的自由性便越發(fā)漫溢而出�����。嘗試給《消息》一個準確的文體定位是枉費工夫的�����,因為這一文本的目的乃是尋求審美上的文體之自由����,創(chuàng)造一種全新的文學性構造方式,獲得了“形式詩學”上的某種解放�����。這也明證著文學創(chuàng)作的“自由境界”��,其“自由的性靈”首先體現(xiàn)在文本的表層�����,即文體的解放��,它擺脫了固有的形式束縛而最終獲得文本世界的徜徉與翱翔����。
題材的自由:
歷史性與社會性
文體上的自由靈活,其內里所反映的則是題材的多樣性���。自1983年“重回商州”并寫下《商州初錄》之后����,賈平凹便在題材的擇取上展現(xiàn)出較具個人特色的“文學趣味”:“商州三錄”體現(xiàn)出一種“見聞錄”的特色,是其行走于商州山地期間搜羅到的諸種生活側面��,不管是《黑龍口》描摹旅途中休憩時的一幕幕鄉(xiāng)間風俗畫�,還是《龍駒寨》以幾乎散文的筆調書寫丹鳳縣城的地理與文化歷史,甚至《劉家兄弟》狀摹三個人物形象���,都是隨時調用題材��,寫來又不拘一格�;到了1990年代的《太白山記》����,取材上更近于中國古代“志怪志人”的傳統(tǒng),寫來全是荒誕不經的口耳相傳故事�,《寡婦》取材于鄉(xiāng)村多見的寡婦門前是非多的奸情、《獵手》以類“善惡報應”的方式寫了一個聽聞中的故事�、《香客》則類似于酒后談資的神怪故事,它們都隨性而至�����、率性而為����,把日常的閑言碎語麇集而來,入于筆下而成篇章����;此一種寫作風格,到《秦嶺記》的出版則臻于成熟�����,且第一次以大規(guī)模的方式集中展現(xiàn)了賈平凹對這種選材方式的得心應手的運用���,文中五十多則小文章既有故事��,也有各種人文風俗的考證與描摹����,甚至有些可以直接入于地方志……此次《消息》的寫作����,再一次將“隨性而至、率性而為”的選材方式運用到極致���,其規(guī)模與篇幅都更為宏富����,顯示出某種不拘一格的創(chuàng)作追求。
《消息》中多數(shù)篇章都是嚴格地按照短篇小說的寫法��,塑造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形象�����、引人入勝的日常故事��,其中較為典型的如第二十則《海坪》描摹了一個機緣巧合不斷升遷的底層小人物形象及其一路走來的喜劇性故事�����;第四十四則《好死》講述名叫阮小手的小人物及其一生與時代的共振故事�����;第五十八則《柳長馬》記錄鄉(xiāng)村好人和他被“眾口一詞”的話語說出的疾病……但整部小說中���,大批量的“志人志怪”小故事構成了核心�����,大約占去一半多�,如第五則《集市》寫的是白日遇鬼后患病的奇事����、第二十七則《桃花命》書寫荒唐離奇的死亡故事、第九十二則《童山狼》中人狼不分的志怪故事等��;第六則《終南山隱者》�、第七則《元龜嶺》、第九則《謝小白》���、第十四則《李三四》���、第三十三則《白城市長》、第五十七則《陰陽先生》�、第五十九則《石生光》、第六十五則《白朗》等等���,又都可以看做是“史記筆法”寫成的“人物小傳”�����。
不惟此�,整部小說還穿插著大量地方散記,構成了類似于“地方志”書寫的內容��。第一則《黃河晉陜大峽谷》純用白描手法��,詳細介紹了黃河在晉陜段的水文地理與兩岸的風俗文化�,它達成了長篇小說開首所常用的“景觀描寫”效果;此后����,這類文字逐漸增多,隨機地排布在小說之中——第三則《三河口》�����、第十則《紫云山》�����、第十二則《安羅鎮(zhèn)》�、第十三則《桃花谷》、第二十六則《商山道》�、第三十則《注水》、第三十一則《臨猗灘》�、第三十六則《丹江》、第四十三則《從黃龍到白水》�����、第五十則《涇河》、第七十三則《西洛水》�����、第七十七則《上鳳凰嶺》等����,讀起來更像是翻閱地方志中關于地理風物的介紹����。
與地理風物相類似,則是眾多取材于地方歷史文化遺跡���、鄉(xiāng)風民俗的眾多片段——第二則《倉頡廟》寫的是洛南縣的文化遺跡�����、第四則《文筆峰下人家》則寫人性民風�����、第十一則《連山》又側重地方物產��、第十六則《雙合墓》與第十七則《獨木寺》以及第三十二則《肅成院》取材于地方歷史遺跡��、第十八則《地主與麥客》則介紹地方風俗的由來����、第二十二則《?窟野人》與第二十三則《鸛雀》以及第二十八則《唐公房碑》寫文物遺跡……此類題材占據(jù)較大篇幅,令人相信賈平凹的寫作得益于各類“地方志”應當不少����。
更有甚者,第七十四則《履歷》則取材于日常簡歷�;第七十五則《緣分》隨手錄下三個飯桌上的閑談;第八十三則《向回報案》以問答的方式實錄報案口供�����,與長篇小說《高興》的開頭大為相似�;第八十四則《玩龍得道》又是無所寫的寫,純粹“閑筆”����;第八十五則《花圈沒花》轉向文壇掌故;第九十一則《斷橋》類似于新聞報道����;最妙的是第八十九則《柳嫂哭靈》和第九十三則《訴苦》�����,實錄一個婦人悲哭丈夫時的言語和一位鄉(xiāng)民進城走親戚時的訴苦��。在題材的選擇上“隨性而至���、率性而為”的特色十分突出,不受任何文體的規(guī)范與約束�����,呈現(xiàn)出“文學的肆意妄為”�,卻總能帶來對人世的深刻認知�。這便是文體的自由與題材的自由所催生出的詩意的自由,或思想的自由���。
詩意的自由:
精神性或思想性
在《消息》的開頭��,賈平凹寫下八個字的“題記”:“百草奮興���,群生消息”。在“后記”中他圍繞書房中的“菩提樹”大書特書,其中有言:“這關乎于病毒與詛咒����,關乎于謠言與詆毀,關乎于陰謀與背叛�。我是經歷過無數(shù)次劫難的,已經不再那么慌張�����,回家來抖抖衣服�����,衣服上落下一地盡是嫉恨的眼珠子��?����!苯洑v磨難后的“曠達”�,構成了《消息》審美風格之一,因此第十九則《凌普渡口》中關于此岸與彼岸����、“我在畫我”、逝者如斯夫的“你把我都畫老了”等,就顯示出一種哲理性的追求——它很容易關聯(lián)于莊子《齊物論》中關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的論述,亦能將之導于莊子泯滅是非��、有用于無用等的“大道”思想與“澄明”境界:“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边@也是為什么賈平凹在《河山傳》的“后記”中一直在強調:“我選題材的時候���,是題材選我��?我寫《河山傳》��,是《河山傳》寫我���?”“錢在我手里�����,是錢經過了我�。”
基于此種“人世間的看透”���,整部《消息》就體現(xiàn)出一種閑散��、飄逸�����、灑脫又帶有肅穆���、莊重與崇高的“詩意形態(tài)與審美風格”。言其閑散����,主要是因為無論文體的自由操練上,還是取材的“隨心所欲”上����,整部小說都似乎處于無所寫的狀態(tài),但寫來卻又都是人間百態(tài)���、生民萬狀�����,既有外在觀察視角的冷眼旁觀�����,亦有內在體悟的物我為一�;言其飄逸、灑脫�,則是為了強調《消息》每一則故事中都隱藏著對生命的深刻體悟,對命運的某種皈依后的隨波逐流����,只不過此一隨波逐流不是躺平、佛系或無所事事���,而是體現(xiàn)出一種本然性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狀態(tài)�����;自然,言其肅穆�����、莊重與崇高,又因為整部作品雖然看上去荒誕不經����、神鬼皆無所避諱,乃至于寵辱不驚�、生死看淡,其內里都包涵著世態(tài)炎涼的冷峻與沉浮得失的沉痛��,一頭牽系著從心所欲的瀟灑�����,但畢竟另一頭還仍舊有著規(guī)矩與方圓的條框����。經由那不意間的點染,來自于人世各種興衰成敗的感慨�����,愈是肅穆��、莊重與崇高�����,就愈是將它所映襯著的自由與灑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于此���,“涅槃重生”的暢快與曠達�����,也就以混合著詩意的思想性����,侵染于文本的字里行間�。非如是,便不能理解第四十五則《碗》中以木碗與瓷碗的命運來隱喻人生的遭際�、第二十九則《沙有金》中的詭譎人生及其悲劇命運,亦難以知曉第三十八則《雁過拔翎》故事的荒誕以及夢境與現(xiàn)實的不可分����、第六十三則《長舌》中繆亂的人世種種以及小人物生存的悲戚……整體上來說,“詩意的自由”背后所隱含著的諸種思想性����、哲理性,追求著一種精神上的超邁與解脫��,實則帶有人世間的“不忍人之心”的屬性����。
《孟子·公孫丑上》中有言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xiāng)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彼^“不忍人之心”又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觀察,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紅塵已苦��,就不必再同類刁難�,以悲憫之心諦視“群生消息”�����,以惻隱之心體悟“百草奮興”��,莊子所言“天地與我共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才能實現(xiàn)����,甚而實現(xiàn)“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后所達到的“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的澄明之境界。只不過莊子“樹之于無何有之鄉(xiāng)廣莫之野”的是大樗之木��,而賈平凹所操持的則是生花妙筆罷了�,殊途而同歸,皆可作為理解《消息》的思想進路。
(作者系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青年評論家)
責任編輯 王順利-《新西部》雜志-新西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