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聞傳播學研究密切關注重大現實問題,深入聚焦理論和實踐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持續(xù)推動研究范式轉換,多維探析學科發(fā)展創(chuàng)新之路��,取得了比較豐碩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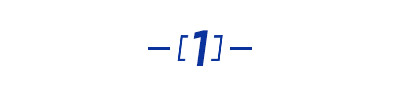
重大主題研究
結合重要歷史節(jié)點和重大現實問題���,新聞傳播學圍繞“建黨百年新聞事業(yè)發(fā)展”及“新時代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兩個重大主題����,展開了集中而深入的研究����。
(一)建黨百年與新聞事業(yè)發(fā)展的歷史經驗
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新聞事業(yè)健康發(fā)展的根本保障。童兵提出����,黨的領導和黨媒事業(yè)同生共長,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黨媒的靈魂與指導思想���,黨的政治領導是黨媒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yè)中發(fā)揮作用的根本保障與不竭動力����。鄭保衛(wèi)、王青提出���,新聞事業(yè)百年發(fā)展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其思想精髓可概括為“堅持黨管媒體”“堅持人民至上”“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tǒng)一”��,這是黨的新聞事業(yè)百年來取得非凡成就的最寶貴的思想和理論成果�。
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是引領百年新聞事業(yè)發(fā)展的思想指南。陳力丹等多維度考察了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來時的路”�����,分析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中的傳播觀及其對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革命的影響���;依據大量珍貴史料原件和訪談�����,展現了列寧《火星報》在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中的傳播軌跡���。鄧紹根以五四運動后《新青年》轉向為中心����,直面歷史爭論�����,重新考察中國無產階級新聞事業(yè)的誕生過程��,追尋百年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yè)的歷史原點和優(yōu)良傳統(tǒng)����。丁柏銓考察了建黨百年來輿論觀的演變軌跡,提出黨的輿論觀在改革開放后進入系統(tǒng)性理論構建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更加體現出系統(tǒng)化、系列化�、創(chuàng)新化的顯著特點,輿論引導“時度效”論���、“同心圓”論等已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的重要構成部分�。季為民考察分析了黨的新聞理論在百年新聞實踐中接續(xù)傳承����、吐故納新的發(fā)展歷程及其歷史邏輯�����。董天策等分析認為�,中國共產黨在百年新聞宣傳輿論工作中先后形成了黨性原則�����、輿論監(jiān)督����、以正面宣傳為主、媒體融合����、現代傳播體系等核心理念���,充分體現出中國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時俱進的理論活力與理論魅力����。馬凌���、劉勝男從中國共產黨早期宣傳觀念����、宣傳組織與宣傳方法的角度,考察分析了宣傳與新聞�、宣傳與鼓動、宣傳與輿論���、宣傳與教育�、宣傳與文藝的關系�。
新聞體制和新聞政策是新聞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王潤澤�、王婉以新中國成立初期新聞總署的成立與撤銷為線索,考察了“黨管媒體”原則形成的歷史背景和過程�����。周慶安�����、劉勇亮提出��,百年來黨的新聞發(fā)布工作經歷了從個體到組織�、從宣傳到對話、從應急到常規(guī)直至成為黨的考核機制的變革����,折射了黨從革命者到治理者的角色轉換�����。姬德強�、朱泓宇從黨際���、國際��、命運共同體三個維度考察了中共百年對外傳播史��,提出對外傳播主體身份的變化見證了中國共產黨角色的傳承���、轉化與發(fā)展。劉小燕���、崔遠航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百年新聞政策的研究圖譜,提供了觀察中共百年新聞政策演變的另種視角����。
新聞實踐研究關注到報刊活動的宣傳動員和修辭策略。陳信凌���、邱世玲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qū)最早建構的新聞宣傳實踐框架及其在“喚起工農千百萬”宏大事業(yè)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提出在“統(tǒng)一的體制與格局”形成前�����,它是新中國媒體運行的先行摸索與成功預演���。周旭東�、徐開彬考察分析了中共早期革命運動宣傳的修辭策略��,提出運動修辭主要是為處于進步潮流和階級壓迫中的勞動者提供“覺醒”和“起來”的合理性�����,《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的開頭“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正是這場辦報活動在修辭層面的延續(xù)和體現����。
(二)新時代國際傳播能力建設
2021年5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新時代如何推進國際傳播實踐與研究�,成為新聞傳播學關注的另一個重大主題。
從宏觀上把握國際傳播的理念和方向具有根本性意義���。胡正榮�、李涵舒提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中���,中國國際傳播的推進應“回到中國”汲取原生文化營養(yǎng)���,構建國家和民族的全球化話語敘事�,在破與立中形塑“可被理解的中國”。程曼麗提出����,新時期中國國際傳播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既要講好“中國故事”�,為西方社會理解中國發(fā)展提供適應性話語�,又要講好“世界道理”,為求解世界性難題提供中國方案�����。姜飛提出�����,利益���、邊界和秩序構成國際傳播變局三大歷史線索�����,當前核心焦點是秩序推動與導向的變局趨勢�,主要表現為對一個平衡��、健康����、可持續(xù)發(fā)展����、最大限度降低不確定性秩序的期待和實踐�����。
“全球中國”成為國際傳播研究新的視角和方法論����。周慶安、盧明江提出�����,國際傳播既是全景式展示中國形象的過程����,又是清晰敘述中國獨特魅力的過程,中國敘事和世界議題相統(tǒng)一是國際傳播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劉瀅提出��,為改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錯位”現象�,應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置于全球視野下進行考量,致力于塑造“全球中國”形象�����。張毓強����、龐敏提出��,未來國際傳播推進的邏輯基點應是“理解中國”“回到中國”��,并圍繞“全球中國”這一邏輯核心打造“可溝通的中國”�����。史安斌等進而認為�����,“全球中國”不僅是全球范圍內正在形成的地緣政治和社會經濟權力形態(tài)�����,也是理解新全球化時代中國國際傳播戰(zhàn)略的“去中心化”方法論����。
推進國際傳播體系和能力建設是關鍵之舉����。段鵬提出���,構建中國特色國際傳播體系離不開理論支撐�,當前國際傳播研究內卷化嚴重�,突出表現為國際傳播研究的熱門和跨文化傳播研究的門庭冷落,存在基礎理論與實踐研究脫節(jié)的狀況�����。孫利軍�����、高金萍探討了國際傳播中“污名化”中國共產黨的深層動因���,提出海外中國學是對外講好中國共產黨故事的重要渠道�����,有助于從外至內共筑中華民族自信��。陳薇以知識社會學作為分析框架�����,探討了基于知識生產��、知識共享和知識對話的國家話語國際傳播新路徑����。李鯉提出���,中國國際傳播轉型升級有待對接全球數字平臺的內在邏輯��,在整體觀視域下思考數字化國際傳播的實踐進路���。宮承波等提出,分眾傳播理念指導下的國際傳播實踐不足以解決國際傳播效能低下的問題���,“分眾傳播”理念需逐步升級為“精準傳播”理念��。

媒介變革���、范式轉換與學科創(chuàng)新
在技術與媒介變革背景下��,如何推動研究范式轉換促進學科創(chuàng)新發(fā)展��,成為影響新聞傳播學未來前景的重要問題�。
(一)媒介變革重塑新聞��、記者�����、新聞業(yè)的認知及邊界
媒介變革深刻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認知觀念��。胡翼青�、張婧妍提出,互聯網使新聞變得更加“常識化”�,新聞邊界走向全面開放,如今很難說清“什么信息不是新聞�,或者什么信息是新聞”。白紅義認為����,數字技術深刻嵌入新聞業(yè)日常運作,導致什么是新聞�����、何為新聞業(yè)、誰是記者等“元問題”發(fā)生了改變��,沖擊和改變著傳統(tǒng)新聞學理論體系�。姜紅、印心悅提出���,當數字技術成為社會構成性要素��,新聞的力量不僅在于“表征”現實或“傳遞”信息,更在于與世界的“交遇”中生成未來���。楊奇光�����、周楚珺提出�,“新聞真實”實現的方式與策略發(fā)生了結構性變革�����,表現為媒介技術層面的“體驗真實”��、認知心理層面的“收受真實”及權力關系層面的“協商真實”�,對新聞真實性的追求從一種專業(yè)準則轉變?yōu)閰f同再造社會集體理性的積極因素��。常江�、田浩考察新聞核心觀念演變發(fā)現����,“真實”逐漸從本質主義概念演變?yōu)椴僮餍愿拍睿翱陀^”的話語消融于新興的情感話語���,“民主”的理念則得到進一步強化�����。
媒介變革對職業(yè)記者的角色地位造成深層次沖擊����。王維佳����、周弘研究發(fā)現,伴隨著西方新聞界全職新聞記者大量被裁員和“零工記者”不斷增加��,平臺壟斷格局下新聞記者的社會角色將從強調公共服務意識的“輿論監(jiān)督者”轉變?yōu)榱髁啃侣勚斜粩祿治鲋涞摹坝嫾と恕薄?strong>徐笛提出���,數字時代記者的職業(yè)邊界日益模糊��,最高層是專業(yè)記者���,其次是業(yè)余記者�����,最底層是信息傳播者��,不同層級傳播者對信息秩序的貢獻和作用各不相同����。王軍��、丁漢青通過問卷調查發(fā)現���,當前新聞從業(yè)者普遍存在著專業(yè)認同危機和自我認知危機,兩者均出現“理想”與“現實”的差異����,對情感認同和從業(yè)意愿具有顯著負面影響。
數字媒介崛起對傳統(tǒng)新聞業(yè)帶來的影響日益顯現�����。姜華、張濤甫提出�,數字媒介解構了封閉化的傳播結構,促動“雜合體新聞業(yè)”興起���,在超限的不確定性中尋求相對確定性��,成為當下及未來新聞傳播實踐面臨的巨大難題���。朱春陽、錢威丞提出�����,媒介融合時代媒體行業(yè)面臨內部整合與整合社會的雙向挑戰(zhàn)����,在“流動的”現代性社會中推進職業(yè)共同體建設,是當代新聞倫理面臨的深層沖突�����。方振武�����、韋路比較考察歐洲12國媒介體制特征發(fā)現,媒介公共所有權增加及公共媒介的市場份額越大����,社會信任情況越好,但媒介市場集中化趨勢超過臨界點則適得其反���。張志安����、冉楨研究發(fā)現�����,對互聯網平臺的依賴成為傳統(tǒng)新聞業(yè)危機��,立足民族國家維系媒體公共性和構建整體性監(jiān)管框架��,應成為政策制定和落實的目標����。
(二)研究范式轉換推動學科發(fā)展創(chuàng)新
技術實踐變革推動研究范式轉換�����,數字新聞學因之持續(xù)升溫。王辰瑤認為�����,數字化技術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和充盈的可能性�����,新聞學研究處在激烈變革的開端��,進入一個新的理論研究生命周期�。常江提出,數字新聞學以“技術—文化共生論”為認識論基礎��,是新聞學在新的技術與歷史條件下發(fā)展出來的新范式���。王斌提出�,從構建關系型知識的角度拓展互聯網環(huán)境下新聞學理論研究路徑�,從本體拓展到范式轉換促進數字時代新聞研究的系統(tǒng)性變革。陸小華認為��,數字新聞學研究仍處在萌芽初起階段�����,數字內容與人的關系構成數字新聞學的基本問題和邏輯起點。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少數學者開始對網絡新聞學之熱進行冷思考。李艷紅提出�,新聞業(yè)究竟如何為社會建立意義和提供知識,是新聞學研究最主要的問題意識之一�,但這一問題意識以及與之相應的框架分析方法在當下研究中卻很少被踐行,導致意義建構成為數字新聞學研究的一個知識盲區(qū)����。黃文森認為,新聞學在方法論層面出現了“數字轉向”和“計算轉向”���,但對于計算方法在何種限定條件下才可能為新聞學研究提供真正有價值的知識或想象力�,需要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探討���。
數字新聞學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路向�,還有研究者從不同角度思考當代中國新聞理論和新聞學的發(fā)展問題��。楊保軍認為��,新聞理論研究的關鍵問題是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fā)����,只有提出能夠引領中國新聞實踐的新聞理論、新聞觀念�����,才能真正談得上為世界新聞理論研究貢獻中國思想���、中國智慧����。當代中國新聞學既要“上升”成為“走向宏觀的新聞學”“走向世界的新聞學”����,又要“下沉”成為“走向生活世界的新聞學”“走向受眾(用戶)的新聞學”。涂凌波提出“以中國為方法”作為新聞理論范式轉換的一種可能�,主張扎根中國經驗、尋求中國新聞理論研究的主體性�����。張壘提出�,中國特色新聞學不僅要能夠指導數字時代的中國新聞實踐��,而且要為數字時代的全球傳播提供中國方案�。吳飛����、楊龍夢玨提出,在不確定性的危機中��,新聞學只有重訪人文主義傳統(tǒng)���,關注技術變革之下的個體境遇���,才能更好促進對新聞業(yè)的重新理解。孫藜提出�����,新聞學欲尋求“突破”或“范式轉換”���,關鍵在于以新的想象力重估舊有“概念”體系���,其中必然離不開對“現代報紙”的重新認識。
學科自主性是學科發(fā)展的動力之源����。趙曙光、劉沂銘基于對1997年至2018年的文獻計量分析提出����,傳播學的跨學科屬性進入新階段,學科交叉引用“逆差”較此前顯著減少��,跨過了施拉姆所言的“十字路口”困境����,成長為具有較強獨立性的學科。鄭欣通過文獻計量分析則發(fā)現���,新聞傳播學領域關于農民工議題研究出現明顯的內卷化現象����,提出要消除“新聞無學”的偏見���,重在走出學科話語圈和舒適圈�����,大力提倡打破常規(guī)�����、開疆辟土的研究�,讓本學科的概念、理論或研究成果能夠嵌入社會�����、日常生活��、現實問題���,這是學科走出內卷化��、走向更加開放的社會科學的努力與希望�。邵國松�、王雪瑩分析認為,傳播研究內卷化有四大表現�,包括問題的封閉性、理論的內衍性��、方法的失衡性�、學科的邊緣性,可從調整經驗研究�、激活批判學派�、強化學科對話��、擴大社會影響等方面進行突破���。
在變革和轉型時代如何把握學科發(fā)展方向至關重要。胡百精從反思學科主體性的角度提出��,構建中國傳播學話語體系須補足重啟傳統(tǒng)的努力�����,人文主義傳統(tǒng)當成為今日傳播學之“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重要支撐�����,即將“人”請回傳播學主場��,關懷人及其作為共在交往者的生命體驗�,追問傳播境況的變化“對人類究竟意味著什么”。杜駿飛提出���,萬物互聯與虛擬社會的演進使“傳播”轉向“交往”�����,“數字交往論”將成為一種面向未來的傳播學���,這種轉向有助于重新發(fā)現理論��。卞冬磊基于當下移動經驗普遍化與傳播學認識論反思��,提出傳播研究應以“移動中的交流”為問題���,重建傳播的交通意涵,走向一個注重物質情境�、超越媒介中心主義、以人類交流為核心議題的開放領域���。祁芝紅�����、李智提出��,如果說“全球本土化”構成了中國傳播學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的來路��,“在地全球化”則構成中國傳播學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的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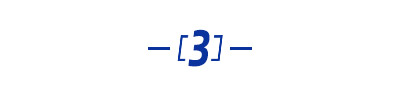
算法、倫理與平臺規(guī)制:
重構技術���、人與社會的關系
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興起����,對網絡輿論生態(tài)、傳播社會倫理及互聯網平臺治理帶來挑戰(zhàn)和沖擊���,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焦點和難點問題,其背后實質是如何反思和重構技術��、人與社會的關系��。
新傳播技術促使網絡輿論生態(tài)發(fā)生深刻變化��。胡泳����、周凌宇提出,網絡空間把關模式發(fā)展為以人工智能和算法把關為主的人機協同作業(yè)��,把關不再以“真相”為導向,而以“任務”為導向��,網絡信息被個人興趣和價值信念所過濾���,“后真相”往往由此而生����。楊洸分析了數字時代輿論極化的癥結�、成因,提出數字新聞生態(tài)系統(tǒng)極易形成觀點集中的景象�����,成為滋生輿論極化的絕佳土壤��。黃文森���、廖圣清將社交網絡新聞生產與擴散概括為“同質連接”與“異質流動”兩種機制�����,研究發(fā)現縱向的“傳播流”源于媒體組織的資源依賴與權力結構�����,強化了上游媒體對于重要信息的外部控制����,從而加劇信息傳播的“極化效應”。周葆華實證分析了輿論演化的“出圈”與“折疊”現象�����,提出健康的輿論生態(tài)體系需要相互制衡的力量與機制��,進入平臺時代更需要機構媒體對事實���、真相和公共利益這些新聞業(yè)核心價值的堅守與實踐����。
網絡輿論演化中的情感因素日趨成為研究熱點��。袁光鋒提出���,中國網絡空間公共輿論呈現出濃厚的情感色彩,這些情感表達塑造了不同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和權力關系��。鄭雯等進而提出����,底層價值取向成為網絡空間好感度的重要指標��,底層群體正以其聲量和影響力形塑著中國的網絡輿論場�����,成為各類社會思潮爭相取悅的對象����。湯景泰等分析發(fā)現����,在2019年爆發(fā)的香港“修例風波”中,虛假信息傳播成為情感動員的關鍵策略�,虛假信息中所蘊含的強烈情感促使示威者完成了對“共同體”的想象,而不同的情感類型又為不同的行動類型提供了動力支持�。徐翔、王雨晨對“今日頭條”進行了樣本分析�,提出網絡空間“自我封閉”帶來的媒介信息內容趨同問題值得關注,網絡公共領域研究要充分審視從網絡局部“巴爾干化”到網絡整體“巴爾干化”的信息異化風險��。
數字勞動研究更多聚焦于“人”的主體性問題���。丁未通過分析深圳出租車司機與“滴滴出行”平臺長達 8 年的博弈歷史�,提出每個生命體都是數字化基礎設施“活的零部件”,所有人的價值都面臨著被數據遮蔽���、異化與吞噬的命運�����,何以安頓身心成為有必要質詢的問題���。張錚等調查顯示,非工作時間社交媒體使用讓媒體從業(yè)者保持隨時隨地的在線狀態(tài)����,繼而逐漸被這種在線時間文化所馴化,成為在生活時間貧乏與工作時間壓力下“被剝削的勞工”�。郭小安、趙海明提出�,如果人們仍然沉浸于媒介塑造的“數字牢籠”而不自知,人的身體和經驗將成為媒介所剝削的生產工具�,陷入一種新型的“異化”狀態(tài)�。李子儀、姬德強認為�����,在算法技術壓制下,“斷開”連接既可比作一種“數字罷工”��,也可視為個體為融入加速社會而選擇的一種“減速策略”�。丁依然提出,隨著數字勞工研究陷入“僵局”��,有必要從關注剝削機制轉向勞動者的主體性��,可對有典型意義的生命故事和勞動經歷(義烏“網紅第一村”���、東北“人人是主播”造就的新經濟模式等)進行民族志研究����。
智能傳播塑造的時空觀促使研究者重新審視人�、媒介與社會的連接關系。喻國明提出�����,未來媒介之“新”是看它是否為人類社會的連接提供新的方式���、新的尺度和新的標準���,從“場景時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媒介進化的本質就是將“人體的延伸”的自由度不斷沿著“向外”和“向內”兩個方向突破��。劉海龍等提出了“網絡化身體”概念�����,認為人的身體既可作為技術系統(tǒng)的“補丁”存在���,又能夠切斷與網絡連接而作為破壞網絡秩序的“病毒”存在�����,由此顛倒了麥克盧漢的經典論斷:媒介不是人體的延伸���,反過來人體成為媒介的延伸。孫瑋����、李夢穎提出,二維碼開啟了媒介勾連社會的新型方式��,“碼之城”的出現說明媒介已經從反映現實�、建構現實��,走向了直接驅動實在的生成,呈現人與技術機器系統(tǒng)的“共創(chuàng)生”����。張成良、王國蕓提出以“云端社群”的概念指稱智能媒介時代人們的生存感知空間和社交關系狀態(tài)���,旨在彰顯一種釋放自然社交天性的開放心態(tài)���。
算法技術帶來的傳播社會倫理問題受到高度關注。陳昌鳳提出�,數據主義正在成為一種流行的意識形態(tài),其所具有的“數據最大化”“信息自由至善”的價值觀���,將人類置于工具化�、從屬性的地位���。申琦�、王璐瑜提出�,社交機器人的算法設計不僅從人類社會中獲取數據、構建模型���,還可能將人類社會中的刻板印象乃至偏見在人工智能中合理化���、標準化�����,對人類社會帶來何種影響亟待傳播學者思量�����。吳靜�、陳堂發(fā)對算法機制下新聞透明性的內涵�����、邏輯及價值進行了分析�,提出應警惕新聞透明性成為一種新的權力規(guī)訓。全燕提出�,算法驅策下文化生產的平臺化轉型帶來了一系列價值危機,包括不平等加劇�����、歧視加深��、文化公共性貶損以及公民身份和道德實踐衰落等。牛靜����、朱政德關注到移動傳播場景的空間正義問題�����,提出除了需要公平分配公民對場景的近用權和退出權��,還應讓公民在相對獨立的私人空間能夠消費“必要的無聊”�,一旦場景把私人空間乃至人體細密地纏裹、浸透�,其也就蛻變?yōu)槭ゾ裥逕捚鯔C的淺薄生命。郭小平�、潘陳青注意到智能傳播中的“社會能見度”問題,提出其主要體現為基于“算法價值”的能見度生產�、基于“推薦機制”的能見度分配、基于平臺可供性的能見度競逐�����。
在平臺治理中如何反制技術和倫理風險成為不斷凸顯的社會問題����。唐緒軍、黃楚新、王丹提出���,平臺企業(yè)發(fā)揮社會價值導向的作用日益重要�����,應發(fā)揮算法治理的積極作用����,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注重數字普惠和數字公平���。顧理平提出,數據隱私侵權的“無感傷害”已成為一個嚴峻而現實的問題����,必須通過法律和技術雙重保護,實現智能生物識別技術有序安全適用��。彭蘭提出����,為防止人們成為算法“囚徒”�,需加強算法開發(fā)者的技術理性和算法倫理培養(yǎng)���,提高算法應用者的算法素養(yǎng)���。方興東、鐘祥銘提出����,互聯網大型平臺之間高筑的“圍墻花園”成為當今互聯網發(fā)展最大的威脅��,平臺治理最緊迫和最突出的是競爭與反壟斷以及隱私與數據保護問題����。曾白凌提出,平臺打開了傳播權力多元化���、社會化的大門�,算法使人淪落為對象與符號而“被傳播�、被組織、被對象化�、被系統(tǒng)化、被支配���、被重塑”����,堅持國家主導、強調平臺媒體責任���、強化個人信息保護成為全球網絡平臺健康發(fā)展的迫切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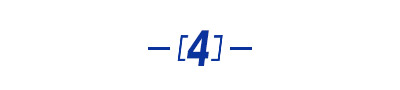
總結與展望
2021年�����,新聞傳播學研究成果可圈可點��。學者緊跟國家和時代發(fā)展步伐��,多角度剖析新技術帶來的傳播和倫理問題��,對熱點問題保持冷思考�����,在看到學科獨立性增強的同時不忘反思研究中存在的內卷化問題�����,這些都是讓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同時也應看到�,跨學科研究成果亮點不多�����,學科反思批判力度不足����,學術理論創(chuàng)構能力不彰�,仍是影響學科發(fā)展的制約因素。
為全面更新知識和理論體系�,研究范式轉換問題成為學科核心關切。這是邁過學科合法性的早期階段�、繼而探求增強學科自主性的必經之途。學科發(fā)展通常會經歷自足���、自立和自主三個階段��,新聞傳播學正處于從自立邁向自主的關鍵時期�����,能否抓住媒介迭代變革的歷史契機���,通過范式創(chuàng)新找到學科發(fā)展的支撐點��,將決定其未來發(fā)展的路向和空間���。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問題是創(chuàng)新的起點,也是創(chuàng)新的動力源�����。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認真研究解決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把握住歷史脈絡、找到發(fā)展規(guī)律���,推動理論創(chuàng)新�?�!庇纱硕裕侣剛鞑W研究范式創(chuàng)新關鍵在于能否“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找準亟待學科回應和解決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
基于既有的研究成果����,未來新聞傳播研究范式創(chuàng)新可突出三個維度:一是從被動走向超越。研究范式創(chuàng)新不能受制于技術實踐變革的維度�����,而應超越技術和媒介二元中介“變量”��,以更加開放的視野回歸和強化人文主義傳統(tǒng)���,深層次思考如何為整合與深化新聞(信息)、人與社會的關系研究開辟新的道路�。二是從內向走向開放。研究范式轉換不能僅限于學科內部知識體系更新���,而應努力吸收其他學科營養(yǎng)����,在跨學科交叉融合中提升新聞傳播學科競爭力和生命力。三是從局部化走向體系化�����。研究范式轉換應努力走出局部化改良路徑�����,緊緊扣住學科核心問題�,對新聞傳播研究領域進行體系化思考,從而找到一條貫通性的范式革命之路�。
新聞傳播學未來充滿生機的學術增長點,將更多來自于跨學科研究和跨學科對話�。新聞傳播學與哲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的結合����,正在推動信息哲學、媒介哲學、媒介社會學��、媒介人類學��、網絡信息法學的興起���,這些新興交叉領域的研究成果對于化解新技術發(fā)展帶來的重大挑戰(zhàn)將會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跨學科對話方面���,黃旦教授在《史林》雜志組織的新聞傳播學與歷史學關于報刊史研究的跨學科對話是一次可貴的探索���,這種具有明確論題且能產出豐厚成果的跨學科對話寄望能夠漸成風氣。
(執(zhí)筆:馮建華�����、王建峰)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法學新聞傳播學編輯部
(責任編輯 王順利)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
掃一掃上新西部網
 不良信息舉報窗口
不良信息舉報窗口



